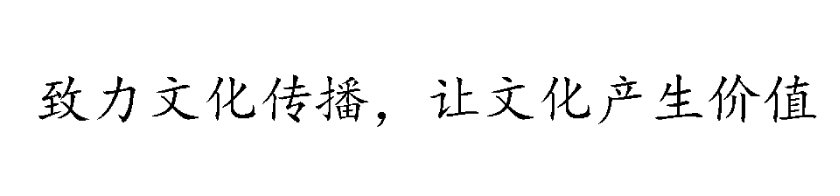中尚圖動態
愛好文學曾經軍人發掘生活出書短篇小說集
時間:2021-10-18 14:40:42 來源:中尚圖

你從未離開
迎風飛舞的身體
像撒在黑夜中的種子
我要和你一起生長
奔向黎明


1--.
薇想把這種感覺說給父親聽,可他不在了。


也許,父親并不想知道這些。
誰知道呢?
·撫慰·


最近,每天這個時刻,薇都陪父親出來散步。天慢慢黑下來的時候,但也不能太黑,沿著107國道一直走到科大,這比原來的距離縮短了三倍可能都不止,可耗用的時間基本和以前一樣。父女間雖沒多少交流,但總會發現些隱藏在日常生活中的有趣事物,路邊新建的房子、新栽的樹以及其他的每日都會出現的變化。還有天氣,每天都更熱一些,日甚一日的熱火朝天的變化。
薇和父親住在干休所,但這里不屬于他們,是爺爺奶奶才有資格住的地方。院子里新建了兩棟灰色的大樓,不過,仍然保留了許多挺占地方的老式平房。那些陳舊的老房子并不奢華,可薇覺得,就是這種陳舊感才留住了以前的榮耀和優越感。往里走,完全脫離了外面的喧囂,甚至于經過的汽車都會小心地放慢速度,沒有人大聲喧嘩或弄出什么聲響,幾個老式的路燈有氣無力地照在路面上,像銀色的沙子。再往前走,拐個彎,就是他們的房子。
從外面看,只有一個房間的燈亮著。的確是這樣,薇的奶奶去世后,這套大房子里就只有他們父女了。更早一點的時候,大部分時間,只有薇的父親一個人住。
電影沒看成。快開映的時候,薇想到了父親。她記得,本來要幫他換內衣的,還要準備他該吃的藥,以及再買一大瓶止血劑。
此刻,薇在門前跺著腳,用馬尾做的像拂塵一樣的東西抽打著褲腳。這不是多此一舉,一部分原因是為了清除灰塵,另外,也是住在這里多年養成的習慣。爺爺他們一直都是這樣,進門前要打掉灰塵,但奇怪的是,他們進屋從來不換拖鞋,即使是回到自己的臥室里。薇想過這件事,也許老人家覺得穿拖鞋會增加某種不確定的危險。而薇保持這樣做的理由,很難說不是一種敬畏,她享受只有回到這里才有的特殊儀式。
當她還在外面的時候,父親已經不行了。


事實上,他一直不舒服。床旁邊的桌子上放著各種藥,胡亂地堆放在老式的錄音機前面。止痛藥吃完了,還沒來得及開新的,其中有幾盒是治抑郁癥的,還有所剩不多的止血劑。后來,當薇收起這些藥準備扔掉的時候,她想象了當時的情景,父親肯定想說些什么,想說什么呢?是怨恨最后的時刻,自己不在眼前,或者是自己出去的那一刻,他已經快失去意識了,還是他一直就這樣躺著,一動不動地看著白色的天花板,盼望那一刻降臨?
父親喝水的杯子已經空了,水沒灑出來,這讓薇覺得有點意外。因為沒來得及換下尿不濕,此刻,父親的身子下面有明顯的水漬。那一刻,他一定很不舒服,可這情況并不算嚴重,他寧愿這樣,也比死了強得多。枕頭旁還有一些攤開的書和一本日記,看來,他并沒有料到死神在那一刻會突然降臨。
天氣不合時宜的溫暖和晴朗,陽光透過窗戶照在客廳地板上。薇開始想象,父親死前經歷的痛苦,或是沒來得及痛苦就已失去了生命。她和父親曾經討論過他的病情,有些話,薇說得不明確,但父親卻不會察覺不到自己身體的變化。他們倆心照不宣,像等著一件將來必然發生的事慢慢逼近。薇設想自己一定會在場的,說不定會像小說或電視劇中描述的那樣,既痛苦又神圣,放著他喜歡的音樂,枕頭和其他物品已擺放好,她穿戴整齊,然后拉來一把椅子。這樣,她就可以拉著他的手,看他斷斷續續地訴說自己最后的心愿或披露一些重大的隱私。她父親會喜歡那種儀式的,只是不喜歡拉著手。最近散步的時候,他對她用力握著的手很不習慣,總試圖掙扎和擺脫,最終的結果自然是徒勞無益,他已經無法僅僅靠自己的力氣步行那么遠了。
“你不要這樣用力拉著我。”
“你有可能站不住。”薇對父親突然的不滿有些不解。
“放手吧,我又不是殘廢。”
“嗯,你不是殘廢?你不是嗎?”薇在心里大聲咆哮著。
他想的大概是如何維護一個父親的尊嚴,病人的尊嚴。而后者更容易被人羞辱和瞧不起,他不想這樣,但又無可奈何。
盡管如此,薇還是感覺突然,太突然了。雖然醫生讓她有心理準備,可她忙得沒顧上準備那些死人要用的東西。墓地是她和三民叔叔一起去買的,父親將和他的父親埋葬在一起,在同一座山上,是一座離此不遠的秀麗的山。這也算一種團聚,不是嗎?
薇不清楚父親到底有沒有留下什么信息。起碼,應該有一份遺囑,盡管他的財產差不多都是從爺爺那里獲得的,不太多,但他應該這樣做吧。大多數時間里,他習慣用筆記錄下自己的計劃。可這次,父親以這樣快又這么不近人情的方式離開,還是讓薇感到了困惑和悲傷。薇和父親曾談論過,忍受無助、痛苦和自我反感的極限,意識到那個極限的可能性和重要性,而不是省略過去或別的什么。


寧可早點,不是晚點。
人生就像行在山路,在某一時刻,被一股有些粗魯的山風吹醒,忽然發覺風景在不斷倒退,同行人或走或停,而自己始終向前,不可改變,無法轉身。
2.
也許應該先坐著他的車,隨便去什么地方。
比如,阿拉善,她愿意去感受一下
那種清涼又令人窒息的無人區。


·三十二立·
店里的裝修風格明顯偏男性化。有兩個女人在聊天,聲音不高,但張揚的東北話毫不收斂,大概聊得不開心,沒有在陌生人或朋友面前應有的禮貌。經過時,健雅瞟了她們一眼,覺得像是兩姐妹,雖然其中一個的臉更嬌嫩,額頭也更寬闊。她們肯定是一起來的,不過坐得不親密,或許正因為什么事情鬧得不愉快。
“你愿意坐在哪里?”一個四十多歲的大叔問,“坐沙發?那兒靠著窗也舒服一些。”然后,他推開柜臺的側門,迎面走來。
健雅注意到了他的手,像做醫生的姑夫一樣,纖細而蒼白。
“有什么要點的嗎?很抱歉,這個時候不能全都供應,不過還是有六七種可以選擇。”他把菜單遞給健雅,“有兩款點心是我今天試著做的,味道還可以。不過咖啡要現磨,可能得多等幾分鐘。”
“那就試試今天的運氣。”健雅點了他推薦的咖啡,又對著窗戶里的自己說,“就當下午茶了。”
健雅這次沒看手機,而是把剛才看的書攤到桌上。沒有人在對面,身后的位子也沒有人,空曠帶來了安全感。此時,她忽然覺得請假看書比看電影更不靠譜,又很快在心里安慰自己,這畢竟是生日的一部分。
健雅拿起咖啡,喝了一口,味道很濃,不過正合她的口味。她決定喝完這杯后再要一杯同樣的。偶遇一杯合心意的咖啡,也是需要緣分的。其實,她一直覺得咖啡比烈性酒更能讓她感到興奮和安慰。
兩個女人懶洋洋地把頭靠在椅背上,看著手機,她們似乎不會愿意被打擾,但也難說。她們的長相和衣著都不錯,應該過得挺好的。健雅取出本子,想在紙上記一點東西。她做編輯前就有這個習慣,隨手記下有趣的事。才三十二歲而已,老了嗎?她想讓自己平靜點,這需要精致和準確的判斷力。


“這是另一種生活方式。”
至少,健雅是這樣認為的。堂妹也發現了這一點,說健雅現在對事物的評判開始高屋建瓴并且無懈可擊了。這幾年,保持同樣的姿勢已經成了她的標簽或某種職責。可她剛剛寫下“生日這天”幾個字,就發現自己無法像往常那樣流利下筆了。光線突然變暗了,窗外的陽光被一層厚厚的烏云遮住了。她放下筆,重新拿起書,任意翻開一頁。這本書,她以前草草地瀏覽過一遍,還像有強迫癥那樣,每隔幾頁就在文字底下劃上杠杠。重讀此書,她發現自以為大有收獲的地方,現在卻顯得晦澀難懂和模棱兩可。
“……若能規定人不得將自己的心不能接受的東西放進腦子里,那么還有什么法律能比這更明智、更公正、更慈悲為懷的呢?”
書從健雅的手里滑了出去,她落入一個夢境。在這個夢里,她和爺爺都很年輕,在一條下雪的路面上,他們每走一步,身后都會留下黑色的腳印,很勻稱但說不上美。雪花變成松軟的、厚厚的地毯。爺爺問為什么。她很自信地說,那是李商隱的五言詩。爺爺笑而不語,不過,笑容和那些腳印融為一體,變得更長了。她明白,也許自己犯錯誤了,爺爺知道答案,只是想考考她。可是,當時健雅沒把握住機會。
健雅醒了。
她清醒時的第一個念頭是不好意思。那個會做點心的帥哥,此刻正站在她的面前。
“你睡著了。”這么說了之后,他笑了,“書都掉地上了。”
很短的夢。可現在夢的內容完全不見了,只有身體殘留著做夢后的疲憊。健雅擔心自己流了口水什么的,不過應該沒有,她想去衛生間整理一番。
“不好意思。”她輕輕拿起了包,不想顯得唐突和過于匆忙。
健雅洗完臉,收拾并調整好心態回來的時候,他已經走開了。
“你嘗嘗這個。”
咖啡是專門做的,一端過來就有強烈的味道竄入健雅的鼻孔。不同的是,他換了杯子,是綠色的穆斯林風格。她抬頭看著他,像是讓他解釋一下為什么。
“嗯。”他捂著嘴,用力地清了一下嗓子。與其說是禮貌,更像一個直截了當但必須要做的交代。他問她,知不知道咖啡其實是阿拉伯人發明的。這是一個有點長并帶有傳說性質的故事,牧羊人發現他的羊群總是莫名其妙地興奮,后來他找到了原因,是羊無意中吃了一株野生灌木的果實。
其實,他也不知道咖啡是什么植物的果實,不過這些不重要。
能夠欣賞遺憾的人,才不會被生活的風浪擊倒。
萬事萬物皆有所缺,我們必須嘗試去原諒,才能在生活的細節中發現更多的趣味和機緣。


3.
應該說,城市屬于那些偶爾或一直落魄
的人,市井和三教九流才保存著
城市的味道。
·風從山那邊吹來·
一年前,楊光明覺得家里開始雜亂無章了,而這種情形一直在變壞,甚至發生了令人擔心的狀況。座機旁的小本子上記著所有事情,買菜、和某某一起吃飯或聊天,還有兒子楊小虎和孫子放學后要來吃她燒的雞翅。若萱并不擅長做這些,但卻樂此不疲。她把時間安排得準確又飽滿,效率不高,但足夠感人。
楊光明困惑的是,她為什么不寫成一張張便箋,貼在相關地方。也許,她沒有覺得自己陷入了某種困境,只是年齡大了,或是她父親去世后,悲傷令她在短期內記憶力不能集中。她可能連這個都不承認,她只是不愿關心那些瑣碎的事情,她是路盲也是臉盲。
但那又怎么樣,即使出門坐錯了方向,她也沒把自己弄丟過。其實,也有更嚴重的事情發生。
有一天,楊光明打算出門的時候,若萱說她想出去走走。
“我可以的,我怎么能辜負這么好的天氣?”
“嗯,不過你可要準備零錢,或者把想買的東西寫在紙上?我還是和你一塊出去吧。”
“你認為我不行?”
她換了衣服,打算買一些楊光明愛吃的水果。
剛進菜場,一只小花貓從她的眼前斜穿而過。她不討厭貓,但不喜歡它凝視人的那個瞬間,讓若萱克制不住地害怕。她走走停停,想起了杰克——她的狗,有它在自己就會有底氣,就不會讓野貓欺負了。可她不知道,那只貓只是碰巧路過而已。
后來,當若萱看到楊光明的時候,她努力不讓眼淚掉下來,她出門時拿了錢,可在門外換鞋的時候又隨手放在鞋柜上。她的手機沒有支付功能,她曾經說過,用手機支付像開車一樣讓人擔心,不安全。后來,她又穿過街道,找到了一家生活超市,問人家可不可以先欠著,后來又說不用了。令人費解的是,她講述買菜忘帶錢的事,像是開玩笑,她知道要買什么,或者選擇替代品,比如錢帶得不夠多的時候。
“我覺得有什么可操心的呢?”她說,“我知道,我的精神并沒像志輝那樣錯亂,只是有點驚恐癥罷了。”
志輝是她的堂弟,去年得癌癥死了,生前有嚴重的焦慮癥。
楊光明問她是不是在吃精神類的藥。
“對呀,有些藥是強制安定情緒的,但我不會像志輝那樣胡來,你說呢?”她說的好像有道理,但有些輕浮。
“我知道我沒問題,不過總有人說我記性不好。”


這是一個大問題,她意識到了,不要像她去世的母親那樣,漸漸地分不清誰是誰了。
“她總是這個樣子。”楊光明對醫生說,“有一天,她想洗了碗之后上樓看書,然后完全忘了。水在屋子里到處亂竄,后來流到走廊上,一部分順著墻根流進了電梯。從那個時候起,我就不讓她洗東西了,我們開始在其他地方過冬天和夏天。嗯,情況似乎有好轉,可她覺得刻意的安排讓她看起來像個笨蛋或弱者,但也接受了這一切。她不喜歡一年四季住在同一個地方,像生活在籠子里的某些動物。”
楊光明一直在留意她的變化。若萱不再記錄,也不獨自去買東西,不過她熟悉自己和兒子所在的小區,她和兒子聊得不多,但能聊到非常久遠的事情,聊出生時的事,在什么醫院和那天的氣溫,但無論怎樣,都沒涉及兒子父親的事。兒子有時也會想,他母親是不是把那段記憶刪除了。
楊光明有次問她:“你知道《新聞聯播》換了主持人嗎?”
“你沒看出來?虧你還天天看。”她說,“如果你真的分不清,下次體檢你也查一下。不過,有個新來的主持人,我叫不出名字。”
楊光明笑了,他知道換了,不過他也不知道名字。可有件事若萱真記錯了,她忘了杰克是哪年離開他們的。
杰克在她的手下生活了五年。
她從狗販子那兒花錢買下它,用心地照料它,但養得并不好。
楊光明說不清是什么原因,他和若萱沒有自己的孩子,這讓他們煩惱但也沒導致他們分開,也許他們應該生一個。結婚的時候,若萱三十五歲。
若萱對現在的結果有一絲不滿和鄙視,不過兒子大了,還有了一個可愛的孫女。
若萱和杰克通常上午出去。杰克的長腿及柔軟的毛發,和它溫暖而不屈服的窄臉很相配,若萱從不擔心它會丟。或許是以前受到的訓斥和懲罰太多了,杰克憂郁的眼睛里藏著不少委屈,可依然忠誠和友善。
不僅僅是家務事,楊光明還獨自打理著旅行社的生意,從南方回來后,若萱找了一個很老實的合伙人。其實賺了錢,但沒人相信若萱能開旅行社。其他人覺得,是因為楊光明那段時間過于孤獨,若萱想讓他振奮起來。她對父母和其他朋友也過分關心了,她愿意獨自承受某些事。
她相信愛。
如果生活之美總是藏在遺憾中
那么,我們不妨做人生的沉浸者。
享受平凡,接納不完美。
.END.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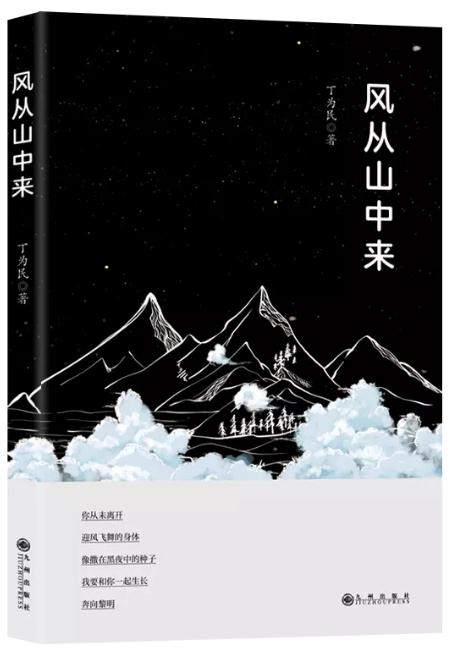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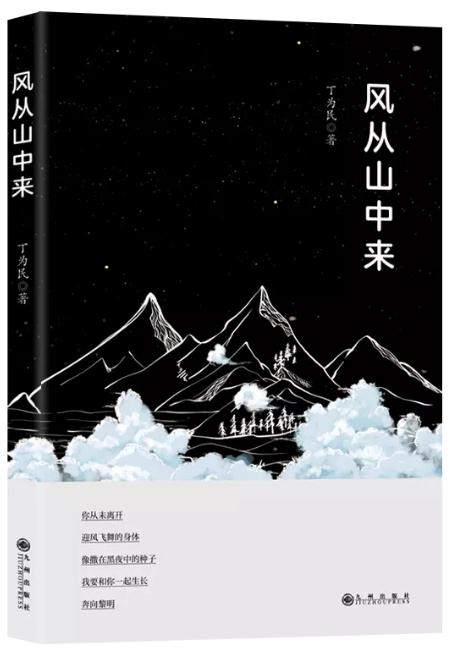
本書為短篇小說集,由九段獨立故事組成,讀者或可從中看到身邊的某些真實的影子,以及作者對于人生的思考,生活的美好總是需要從苦痛中挖掘,而我們最擅長在挖掘的過程中實現自我療愈。
關于本書
丁為民,出身軍人家庭,亦曾身為一名軍人。目前定居深圳,多年來依然保持著對文學的尊重和喜愛。已出版作品《和歲月一起散步》。
>>中尚圖動態